原创 马志明41岁才拜师,明明寿字辈还有人健在,凭啥说能拜的就俩?
换作别人,这事压根儿不会成问题。拜个师嘛,鞠个躬磕个头,走个形式而已。
可落在马志明头上,问题就来了。因为他爹是马三立。
相声界那个谁都得打点儿起精神、别抖机灵的那一位。

说好听点,马志明是世家子弟;说难听点,他一出生就站在了相声界的塔尖儿,一举一动,下面看着的全是人。
所以,他要拜师,不是选个老师,而是给整个相声界立规矩——你马三立的儿子,拜谁,怎么拜,拜哪门哪派,背后全是人情、门户、名望的大博弈。
问题来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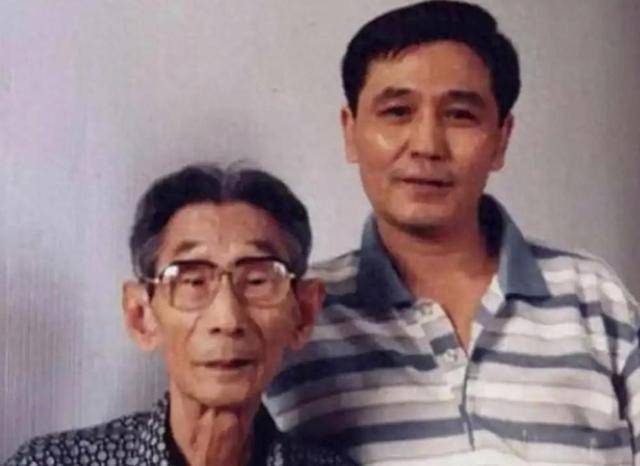
1986年,马志明41岁,终于拜了师。事后采访时他说:“能拜的,其实就俩人。”
网友翻了老黄历一看,寿字辈还健在的明明不止两个,你说这话不等于打脸么?
不急。往下看,咱今天就不讲规矩了,咱来掰扯掰扯这摊事的“人话版本”。
别看有几位“寿字辈”活着,真正能拜的,不一定是活的
这事你得从相声的“行规”看。
相声这行讲“德寿宝”,一代一辈,名字里按字排。马志明是马三立儿子,马三立呢?德字辈马德禄的亲儿子,徒承周德山。
所以按谱系来讲,马三立是“寿”字辈。那马志明想拜师,必须往上拜——寿字辈。
不能低一辈,也不能跨门入派。得按家谱走。这就已经筛掉90%人了。

到了1986年,寿字辈早走了一大批。真正“人活着、辈对、身份够、面子能扛得住马家”的,就只剩下俩人:一个是郭荣启、一个是陶湘九。
别的呢?要么是“活是活着,但你不敢拜”;要么是“名头不够,你拜了掉价”;还有的,说白了——“你家里人不愿意你去磕这个头”。
于佑福?您别开玩笑了,那是自家嫂子

于佑福那会儿也健在,寿字辈,高家门,老一辈也都知道。
可问题是,她是谁?马三立堂弟马四立的媳妇,按辈分算是“家里人”。
咱就问一句,你要是马志明,你能开口拜自家嫂子当师父吗?
这要是传出去,不光江湖人笑话,连老天津卫的胡同大爷都得竖耳朵:“哎呀,马家这事儿怪咧!”

更现实一点,于佑福是女的,相声圈那时候讲得还挺狠:女的可以拜师,但不适合收徒。你要真拜了,谁还认这门?将来你收徒,人家认不认?下不下得去脸来学?
而且她那一门(高家门)当年已经是**“破落户”**了,你马家这金枝玉叶的,往人家门里一蹿,谁看了不觉得不合适?
祝景荃?东北的角儿,拜他=“掉份儿”
祝景荃,也是寿字辈,东北四大荃之一,听起来也有来头,照理说也能拜。
但问题是:他在东北,不在主流圈子。
相声这行,不像搞科研讲成果,讲的是“你在哪儿混圈子”。你要是在天津、北京混出来的,那你有谱。你要是在长春、沈阳讲的再好,也就那回事。

马志明是天津“马家的人”,你叫他跑东北去拜个地方角儿,不尴尬吗?
咱就不拐弯了说:不是祝景荃不行,是你身份不对等。
拜了,反而惹得行内人冷嘲热讽:“马志明找不到合适的,只好东拼西凑混一拜。”
他爹马三立要是真让他这么干,那可不是“谦虚”,那是把马家牌坊自己推了。
郭荣启?这人够格,可你俩不说话
郭荣启那是寿字辈的正牌大佬,能耐不比马三立差,门风也硬,资格也老。
问题是,他跟马三立有私仇(或者至少是多年不来往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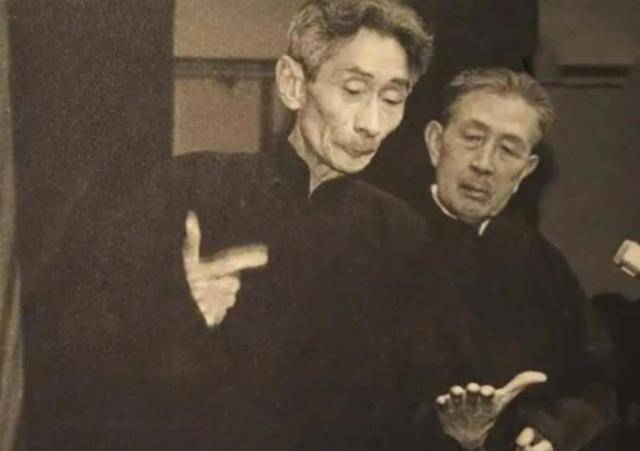
人都在天津一个团里干活,照面都点头不打招呼的,这得是多生分你说说?
马志明自己也说了:“我们家跟他家不走动。”
那拜师就不行了。你说我在街上看你都不打招呼,回头给你磕头?你敢收我,我还真不好意思拜。
所以纸面上,郭荣启是能拜的,但实际上,他“死得比谁都早”。
陶湘九?这是“下下之选”,实在没人选了才选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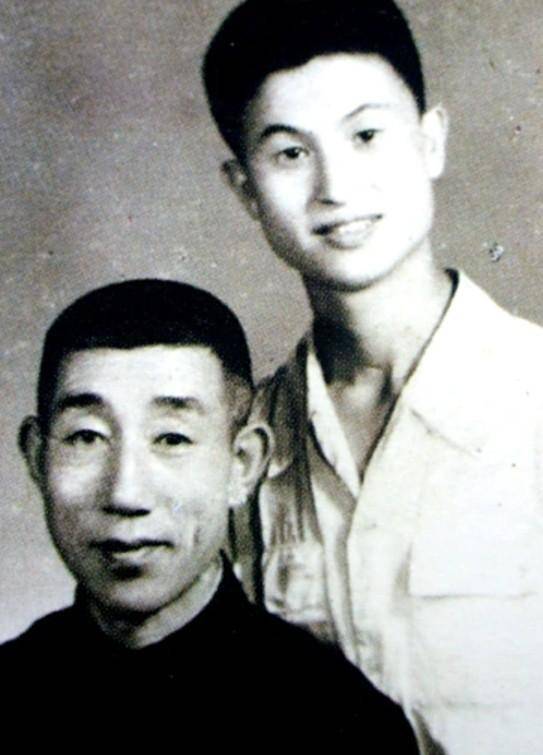
那最后就剩陶湘九一个人了。
这人为啥能拜?因为他:一:真是寿字辈;二:没得罪过谁,脾气好;三:名头虽不大,但也不是小角色,撑得住场面。
但问题也有:
他名气不够,江湖地位不高,撑不起“马家长子的拜师仪式”;
地理太远,不在天津,北京圈,也没太多人能帮你“做保”。
所以马志明虽然口头说“陶湘九也能拜”,但他爹可能心里清楚:这人不能真拜,只能说说。
这就像——“你找对象,剩了仨,俩你看不上,剩一个你说‘也还行’,但你妈心里:‘这门咱不配!’”
于是,才有了“侯宝林代拉师弟”这条出路

最后,拜谁都不合适,那怎么办?
走个“侯宝林代拉”的形式——也就是不拜寿字辈了,咱绕个弯,让侯宝林帮忙牵线,算是补上了仪式,不掉身份,又交了规矩。
别小看这条线,侯宝林虽然是宝字辈,但地位在整个相声界是“山顶上的山”。

更何况他是马三立的“代拉师弟”,这就等于说——你儿子我来做保人,我兜底,你们马家脸面、辈分、规矩都过得去。
你看,连侯耀文都不是拜侯宝林,而是拜了赵佩茹,不也是侯宝林做的安排?
相声这行,脸面是第一规矩,规矩是第二脸面。
总结句人话:
1986年,马志明41岁了,终于拜了师。事后他说:“能拜的,就俩。”

这话没说错。不是活着的就能拜,是你得:辈分对得上,身份兜得住,人情过得去,江湖说得响。
你别说那年还活着四五个寿字辈——活着不代表能收你,名声不代表能配你,关系不对,拜了也是笑话。
这才是真相。
